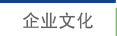崗底人的精神
今年我前去參加民革在崗底村組織的一次培訓活動,課余時間,在李保國教育基地廣場上遇到了另外一群前來培訓的人,其中一個聽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,閑話聊天,一來二去我們就說到了崗底村,那個人指著崗底村說,這是崗底村,也不是崗底村。聽到這話我猛一驚,這說的不是廢話嗎?后來一想說此話必有其原因,于是趕忙虛心討教,他說:崗底村不是一個簡單的村子,已經賦予很多文化,已經成為一種精神象征。
他的話讓我想了很多很多,也常常去思考崗底的過去,更多的是注意觀察今天的崗底,特別是崗底村的崗底人,想從他們身上,從這些農民的身上找到那些所謂的精神象征。
記得第一次來崗底村的時候,那是蘋果熟了的季節,朋友邀我前來摘蘋果,走進果園,看著樹枝上葉子已經稀疏,枝頭上掛著一顆顆大紅蘋果,就像紅燈籠一樣非常好看,使我不忍把它摘下來,不忍把這種美好的景象破壞掉。
從那一次始,我知道崗底村是一個生產種植蘋果的村莊,此后的日子我經常注意這個村莊的人與事。
那一年,我接到了《太行山最綠的地方——前南峪》一書的撰寫任務,使我有機會到前南峪進行調研,在那一次調研中我被前南峪老書記郭成志所感動,這個山村是在這位老人的帶領下,立志改變山區面貌,奮戰數十年,三年搞綠化,六年治河灘,三年修水利,八年完成十條經濟溝的建設,他們用抗大精神開始了極其艱難而又漫長的創業歷程。后來,前南峪村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,讓荒山變成了綠山,成為太行山最綠的地方,成為太行山區黨領導村民進行共同富裕的一面旗幟。
也是在那次調研中,我聽到李保國這個名字,沒有想到因為李保國竟然又與崗底村相遇,結緣。
李保國來到崗底村也不是一個偶然,而是與另一個村支書有緣,這個人就是擔任崗底村黨支部書記的楊雙牛。這個退伍軍人,這個山里的漢子,看似普遍卻在身上藏了堅毅的性格、超前的創新理念,還有一雙善于捕捉機遇的眼睛。
一次機遇讓李保國和楊雙牛兩個人相遇,志趣相同地去干一件種蘋果的事。一個善于領導、組織、發動,一個善于教授,把科技與果樹結合起來,兩個人就這樣合作起來,攜手走了20年,把一個貧困的崗底村變成一產有特色,二產有發展,三產相融合的富裕的崗底村。
我與李保國教授有過幾面之緣,而第一次見他的時候,是在南和紅樹莓種植基地。朋友與我說李保國老師正在這里,讓我也認識一下這位教授。此前我見到過很多教授學者,都是翰林子墨的先生,而我這次見到李保國,當他從樹叢中站起來的時候,我心里猛然一驚,這哪里是一個大學教授?分明就是一個農民漢子,特別是那嘴上的胡子讓我記憶很深,不免心中有了疑問,這是大名鼎鼎的李保國教授嗎?而他確實就是李保國,是真正的李保國。后來我聽朋友們說他的故事,說他在崗底村的昨天,說到他的性格,談他的為人,這些讓我感覺到他的血肉都是那樣普通,又是那么特別。
后來的一次,我們在一起吃飯,當聽到他一天的行程,看到他一天的勞累,還要去趕已經約好的授課,不由和朋友們一起勸他,要悠著點,要注意自己的身體,不能太辛苦了。
那一天是我最難忘的日子,朋友打來電話說,李保國老師走了,我還不解地問道,是又從邢臺走了?朋友說是因為他種的蘋果好吃,去天上種蘋果了。我聽后愕然無語,他走了,走了!再也見不到這位看似平凡而又不凡的農民教授了,那天我的心就像掏空了一樣難以名狀。
李保國走了,卻留下了太行山的新愚公精神,這種精神和這個小山村同在,和這里的果農同在,和這里的今天和明天同在。
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大力發揚孺子牛、拓荒牛、老黃牛精神,并賦予孺子牛以“為民服務”、拓荒牛以“創新發展”、老黃牛以“艱苦奮斗”的深刻內涵,這讓我想到了崗底村的帶頭人、黨總支書記楊雙牛。
那時,那天,那刻,楊雙牛從剛剛擔任村黨支部書記的那年起,他就用“雙牛”精神要求自己,在35年間甘心做“老黃牛”,帶領著崗底村的村民從一個貧窮山村走到了今天,實現了目前人均收入4.5萬元;用“拓荒牛”精神實現了蘋果產業的一產二產高質量發展,創立了“富崗”品牌,組建了富崗集團。又是在這一天,這一刻,崗底村兩委完成換屆,有了新的領導班子,他說了那么多的衷情的話,反反復復在講一個道理,就是要聽黨的話,帶領崗底村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,實現崗底村鄉村振興的夢想。
他的話,讓我想到古代“牛”的精神,孺子牛的典故。
“牛”是先秦時期的大牲,也常常用于祭祀。所以許慎說“牛,大牲也。牛,件也。件,事理也。”又言,牛為大物,在《易經》中稱:“坤為牛”,并解釋說:“地勢坤,君子以厚德載物。”意味著牛是滋養萬物的大地的象征物,說牛有“厚德”之性。可見,遠在先秦時期,牛,真的是很牛了。
牛,在先秦時期不僅用于農業耕作,更重要的是用于祭祀之中。在《禮記》中說:“凡祭宗廟之禮,牛曰一元大武。”祭祀等級中,第一等級是“太牢”,第二等級是“少牢”。“太牢”,就是祭祀社稷時需要牛、羊、豕備齊,而“少牢”只用羊和豕,沒有牛。我們從“牢”字也能看出牛在祭祀中的地位。
人類很早就開始使用牛。《易經》說“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……服牛乘馬,引重致遠,以利天下。”這就是說牛和馬在黃帝時期就作為交通工具。
從這些文獻記載中可以知道,牛,最大的精神就是犧牲,就是去用它的身軀去奠基;又在需要的時刻,又會用它強壯的身體去“引重致遠,以利天下”。
“孺子牛”典故出自《左傳》的記載。春秋時,齊國的國君齊景公有一個兒子叫孺子,長得聰明伶俐,活潑可愛,那時齊景公已到花甲之年,卻經常和孺子一起玩樂,做游戲,孺子要他干什么,他就干什么。
有一次,孺子要齊景公裝作一頭牛讓他牽著玩,齊景公立即讓人拿來一根繩子,繩子的一頭他用牙齒咬住,繩子的另一頭讓孺子牽著。孺子高興極了,便像牧童一樣牽著“牛”猛跑起來,齊景公扮著牛一邊叫一邊跑著,跑著跑著,孺子突然一跤跌倒,齊景公沒有防備,咬著繩子的門牙竟被拽掉了一顆,頓時滿嘴鮮血直流。孺子“哇”的一聲大哭起來,齊景公顧不得自己,而是上前把孺子拉到懷里去安撫。
這個故事雖然是說父母對子女的疼愛,但從另一面卻說明了老一輩心甘情愿的為后輩人去服務,去扶持。“俯首甘為孺子牛”,這是魯迅先生對“孺子牛”精神的升華,是用于比喻心甘情愿為人民大眾服務,無私奉獻的人。
從崗底村到富崗蘋果生產基地,從富崗蘋果到子水科技,從富崗的員工到崗底的果農,讓我理解了崗底不僅僅是一個村莊,更是一種精神的存在,在這里有李保國的“太行山上的新愚公精神”,也有艱苦奮斗的“老黃牛”精神,還有創新創業的“拓荒牛”精神。在這里還看到崗底村的未來和明天,一群黨員,一代新人,甘心服務,用“孺子牛”精神,肩負著鄉村振興的使命,帶領群眾走共同富裕道路,奮斗一直在路上,在肩上,在心上。
今天,崗底村的鄉村振興工作已經開始了,新的規劃,新的發展已經啟動,5G搭建了新的發展平臺,鄉村旅游、遠程醫療與李保國生態大花園建設等等給大家帶來新寄望;新的一代崗底人又開始新的征程,這是一個新的開始,新的長征,新的希望。愿崗底精神永存,永駐,成為這個小山村的前進的動力。